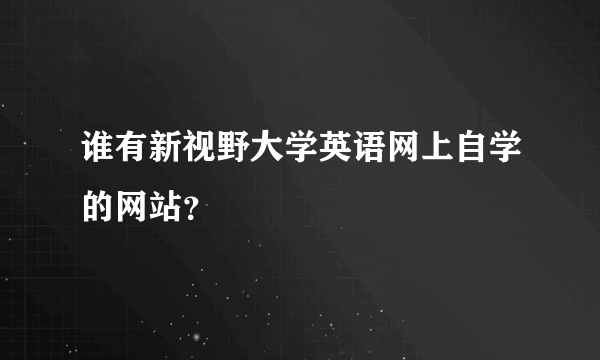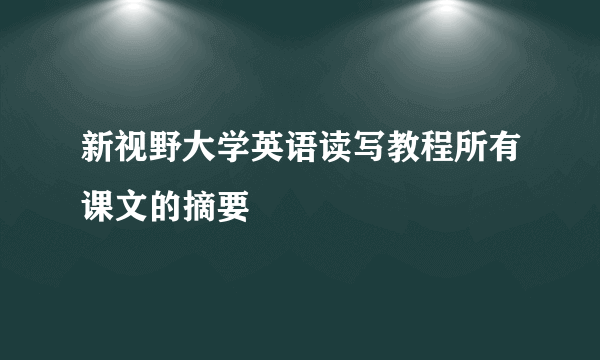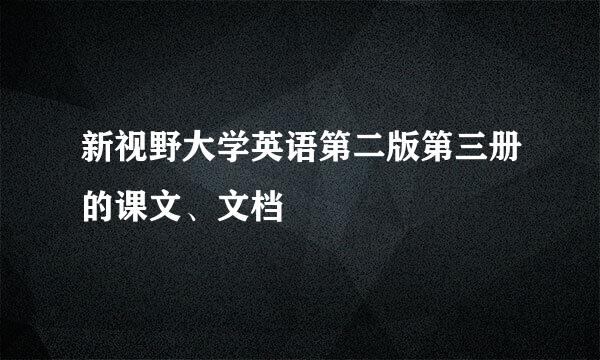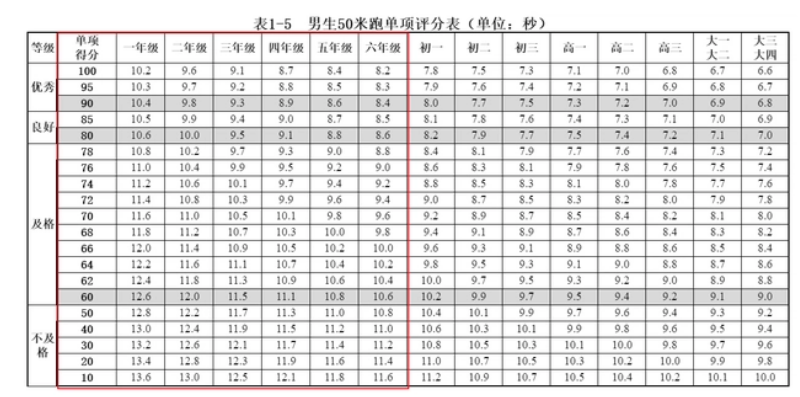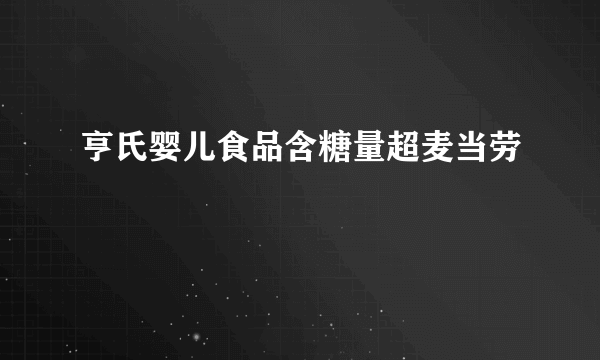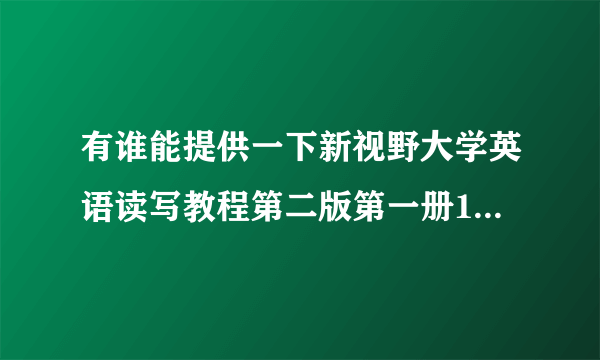
Unit1_passage_chinese_a
美国人认为没有人能停止不前。
如果你不求进取,你就会落伍。
这种态度造就了一个投身于研究、实验和探索的民族。
时间是美国人注意节约的两个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劳力。
人们一直说:“只有时间才能支配我们。”
人们似乎把时间当作一个差不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对待。
我们安排时间、节约时间、浪费时间、挤抢时间、消磨时间、缩减时间、对时间的利用作出解释;我们还要因付出时间而收取费用。
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许多人都深感人生的短暂。
时光一去不复返。
我们应当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外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很可能是: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常常处于压力之下。
城里人看上去总是在匆匆地赶往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商店里他们焦躁不安地指望店员能马上来为他们服务,或者为了赶快买完东西,用肘来推搡他人。
白天吃饭时人们也都匆匆忙忙,这部分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生活节奏。人们认为工作时间是宝贵的。
在公共用餐场所,人们都等着别人尽快吃完,以便他们也能及时用餐,
你还会发现司机开车很鲁莽,人们推搡着在你身边过去。
你会怀念微笑、简短的交谈以及与陌生人的随意闲聊。
不要觉得这是针对你个人的,
这是因为人们都非常珍惜时间,而且也不喜欢他人“浪费”时间到不恰当的地步。
许多刚到美国的人会怀念诸如商务拜访等场合开始时的寒暄。
他们也会怀念那种一边喝茶或喝咖啡一边进行的礼节性交流,这也许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一种习俗。
他们也许还会怀念在饭店或咖啡馆里谈生意时的那种轻松悠闲的交谈。
一般说来,美国人是不会在如此轻松的环境里通过长时间的闲聊来评价他们的客人的,更不用说会在增进相互间信任的过程中带他们出去吃饭,或带他们去打高尔夫球。
既然我们通常是通过工作而不是社交来评估和了解他人,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谈正事。
因此,时间老是在我们心中滴滴答答地响着。
因此,我们千方百计地节约时间。
我们发明了一系列节省劳力的装置;
我们通过发传真、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与他人迅速地进行交流,而不是通过直接接触。虽然面对面接触令人愉快,但却要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马路上交通拥挤的时候。
因此,我们把大多数个人拜访安排在下班以后的时间里或周末的社交聚会上。
就我们而言,电子交流的缺乏人情味与我们手头上事情的重要性之间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关系。
在有些国家,如果没有目光接触,就做不成大生意,这需要面对面的交谈。
在美国,最后协议通常也需要本人签字。
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电视屏幕上见面,开远程会议不仅能解决本国的问题,而且还能通过卫星解决国际问题。
美国无疑是一个电话王国。
几乎每个人都在用电话做生意、与朋友聊天、安排或取消社交约会、表达谢意、购物和获得各种信息。
电话不但能免去走路之劳,而且还能节约大量时间。
其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电话服务是一流的,而邮政服务的效率则差一些。
有些初来美国的人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其他国家,在他们的国家,人们认为工作太快是一种失礼。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花一定时间来处理某件事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给予适当的重视。
因此,人们觉得用的时间长会增加所做事情的重要性。
但在美国,能迅速而又成功地解决问题或完成工作则被视为是有水平、有能力的标志。
通常情况下,工作越重要,投入的资金、精力和注意力就越多,其目的是“使工作开展起来”。
Unit3_passage_chinese_a
我和盖尔计划举行一个不事张扬的婚礼。
在两年的相处中,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起伏,这是一对情侣在学着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时常常出现的。
但在这整整两年间,我们坦诚地面对彼此性格中的弱点和优点。
我们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不但增强了我们的关系,还教会了我们要彼此宽容、谅解和开诚布公。盖尔有时不明白为何我和其他黑人如此关注种族问题,而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好像忘记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仇恨种种微妙的表现形式。
对于成为居住在美国、异族通婚的夫妻,我和盖尔对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相互信任和尊重才是我们俩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许多夫妻因为错误的理由结了婚,结果在10年、20年或30年后才发觉他们原来是合不来的。他们在婚前几乎没有花时间去互相了解,他们忽视了严重的性格差异,指望婚姻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希望避免重蹈覆辙。事实更说明了这一点:已经结婚35年的盖尔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充满怨恨、令人痛苦的婚变,这件事给盖尔带来了很大打击,并一度给我们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当盖尔把我们计划举办婚礼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她遇到了一些阻力。
她的母亲德博拉过去一直赞成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开过玩笑,问我们打算何时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抱外孙了。
但这次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时,她没有向我们表示祝贺,反而劝盖尔想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么说我跟他约会没错,但是如果我跟他结婚,就错了。妈妈,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盖尔后来告诉我她曾这样问她母亲。
“首先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时我对异族通婚是有保留意见的,也许你甚至可以把这称为偏见。
但是当我见到马克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既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年轻人。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脸上有光的。
所以,这事跟肤色没有关系。
是的,我的朋友们会说闲话。
有些朋友甚至对你所做的事表示震惊。
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不同。
因此你要明白,马克的肤色不是问题。
我最大的担心是你也许跟我当初嫁给你爸爸一样,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嫁给马克。
当年我和你爸爸相遇时,在我眼中,他可爱、 聪明、富有魅力又善解人意。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兴奋。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婚姻会天长地久。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结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我所爱的人——你的爸爸。”
“但是我和马克呆在一起已有两年多了,”盖尔抱怨道。
“我们俩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们彼此多次看到对方最糟糕的一面。
我可以肯定时间只能证明我们是彼此深情相爱的。”
“你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再等一等没坏处。你才25岁。”
盖尔的父亲戴维——我还未见过他的面——以知事莫若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决定。
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和盖尔母亲的问题相同:“干吗这么匆忙?这个马克是什么人?他是什么公民身份?”
当他得知我办公民身份遇到了问题时,就怀疑我是因为想留在美国而娶他女儿的。
“不过爸爸,你这话讲得太难听了,”盖尔说。
“那么干吗要这样着急?”他重复地问。
“马克是有公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在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盖尔辩解道。“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结婚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如果我对任何事情有怀疑,我完全可以取消我们的计划。”
她父亲开始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异族通婚的离婚率比同族结婚的要高,而且还列举了接受过他咨询的、在婚姻上有麻烦的异族通婚夫妇的例子。
他问道:“你考虑过你将来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的苦难吗?”
“爸爸,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不,当然不是。但你必须得现实一点。”
“也许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谁的孩子不会呢?可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将会永远拥有,那就是我们的爱。”
“那是理想主义的想法。人们对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是会很残酷的。”
“爸爸,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操心的。但是假如我们在做什么事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什么都干不成了。”
“记住,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都不晚。”
Unit4_passage_chinese_a
大中央车站问询处桌子上方的数字钟显示:差六分六点。
约翰·布兰福德,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军官,眼睛盯着大钟,看确切的时间。
六分钟后,他将见到一位在过去13个月里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女人,一位他素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始终给予他力量的女人。
在他自愿参军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这位女子寄来的书。
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祝他勇敢和平安。
他发现自己很多参军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位名叫霍利斯·梅内尔的女子寄来的同样的书。
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勇气,也感激她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支持,但只有他给梅内尔女士回了信。
在他启程前往海外战场战斗的那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
站在即将带他进入敌人领地的货船甲板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来信。
13个月来,她忠实地给他写信。
即使没有他的回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从未减少过。
在那段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她的信鼓励着他,给予他力量。
收到她的信,他就仿佛感到自己能存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他相信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当他向她索要照片时,她却婉然拒绝。
她解释道:“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和真诚的,那么我长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很漂亮,我会因为觉得你爱的只是我的美貌而时时困扰,那样的爱会让我厌恶。
假如我相貌平平,那我又会常常害怕你只是出于寂寞和别无他选才给我写信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阻止自己去爱你。
当你来纽约见我时,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记住,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停止或继续下去──如果那是我们的选择……”
差一分六点……布兰福德的心怦怦乱跳。
一名年轻女子向他走来,他立刻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她身材修长而苗条,漂亮的金色长发卷曲在小巧的耳后。
她的眼睛如蓝色的花朵,双唇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毅。
她身穿别致的绿色套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
他向她迎去,完全忘记了她并没有佩戴玫瑰。看他走来,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热情的微笑。
“当兵的,跟我同路?”她问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步。然后,他看见了霍利斯·梅内尔。
她就站在那少女的身后,一位四十好几的女人,头发斑斑灰白。在年轻的他的眼里,梅内尔简直就是一块活脱脱的化石。
她不是一般的胖,粗笨的双腿移动时摇摇晃晃。
但她棕色的外衣上戴着一朵红色的玫瑰。
绿衣少女快速地走过,很快消失在了雾中。
布兰福德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压缩成一个小水泥球,他多想跟着那女孩,但又深深地向往那位以心灵真诚地陪伴他、带给他温暖的女人;而她正站在那里。
现在他可以看见,她苍白而肥胖的脸上透着和善与智慧。
她灰色的眼中闪烁着温暖和善良。
布兰福德克制住跟随年轻女子而去的冲动,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的手抓着那本在他去战场前她寄给他的书,为的是让霍利斯·梅内尔认出他。
这不会成为爱情,但将成为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可能比爱情更不寻常的东西──一份他一直感激、也将继续感激的友情。
他向那个女人举起书。
“我是约翰·布兰福德,你──你就是霍利斯·梅内尔吧。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见我。
我能请你吃晚餐么?”
那女人微笑着。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她答道:“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刚走过去的那位──请求我把这朵玫瑰别在衣服上。
她说如果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公路附近的那家大餐厅等你。
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Unit8_passage_chinese_a
人们常常说:对于青春来说,最令人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青春在年轻时被浪费掉了。
在读一份对大学一年级新生作的调查报告时,我又想起了这种惋惜之情:“要是当初我就懂得了现在我领悟到的东西该有多好!”
这份调查报告印证了我以前根据在梅肯和罗宾斯住宿中心对学生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所作的推断:学生们认为如果某种东西(不管它是何物)没有实际意义,不能把它当酒喝、当烟抽、当钱花,那么“它”就基本毫无价值。
基于对188,000多名学生答卷的调查表明,当今的大学新生比这项民意测验开始1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的大学新生都“更主张消费主义,同时也少了些理想主义”。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学生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上的富裕”。
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树立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已不那么重要了。
这一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此,如今最受欢迎的课程不是文学或历史,而是会计学。
如今人们对当教师、社会服务和人文学科、还有种族和妇女研究的兴趣都处于低潮。而另一方面,攻读商科、工程学及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人数却在迅速增加。
还有一件事也不令人意外。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化工公司的销售代理)在干这份工作的第一年所挣的钱就已是大学教师薪水的两倍了──这甚至还是在她修完两年制的准学士学位课程之前的事。
她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我会对他们讲,他们学习音乐、历史、文学等等有什么用!”那还是四年以前呢,我都不敢想象她现在赚多少钱。
坦率地说,我为这位小姐感到骄傲(不是为她的态度,而是为她的成功)。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我们就不能教会人们既懂得谋生,又懂得人生么?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对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制度的否定。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年龄和成熟所能带给人们的启示。大多数年龄约在30至50岁之间的人都会最终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为某个公司、某个政府机构或任何其他单位服务。
我们大多数人最终会认识到,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是由资产负债表来决定的。诚然,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富裕点。但是我们还希望对自己职业范围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我们希望能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效劳。
如果说人要到步入中年才能对人生的含义有所领悟的话,那么为这种领悟扫清障碍不正是教育机构的责任吗?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怨恨从他们工资中扣钱交社会保险金,然而好像只是短短几年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正焦急地站在信箱旁边(等待养老金支票)了。
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最好是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但同样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之外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
而且正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在其他领域的贡献――不管是科学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我们的人生才更完善。
同样地,我们在了解他人的智慧的同时,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
也许更重要的是,教育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了眼前的需求,并使我们看到了事物间的联系。
我们每周都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消息:工会在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罢工,结果却只是使他们的老板破了产。
没有了公司,也就没有了工作岗位。
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目光是何等地短浅!
但是赞成全面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学习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同时,我们也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感。
最近我看了一幅漫画,描述了几个商人坐在会议桌周围,看上去困惑不解的样子。
其中的一个正通过内部通话设备讲话:“巴克斯特小姐,”他说,“是否可以请您叫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来?”
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确确实实是教育应该做的事。
我认为教育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一位大学室友──现在是纽约一家大型航运公司的总裁──过去曾主修过商科,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他也曾在大学调频电台上主持过一档古典音乐节目,并且在学习会计学的时候还在欣赏瓦格纳的音乐作品。
这就是教育之道。奥斯卡·王尔德说得好: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才能用于工作,而把我们的天赋投入到生活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满足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渴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学生能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人生的意义远远不止是工作。
Unit9_passage_chinese_a
“孩子,起来,做个有出息的人!”虽然母亲已经过世,但她的话依然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就如我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样。
她心里也许是为我好,但那时依我看来,她那毫不温柔的为母之道就如同用竹条鞭笞一般严厉。
“天哪!”我叫道:“我已经是个有出息的人了。我有权晚点起床了。”
“要是有什么我不能忍受的东西,那就是逃兵。”她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让我无法拒绝,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的父亲在婚后5年就过世了。
他死后,我母亲没有钱。
她要抚养三个孩子,还有一身的债务。
当时母亲刚上大学,却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几个月后,我们失去了房子,母亲一无所有,只有支离破碎的生活残局等着她去收拾。
我那奄奄一息的精神失常的祖母不得不被送往疯人院,而我们也只能寄居于她弟弟艾伦的家中。
最终,母亲找到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每周工资10美元。
虽然母亲期望我能成为百万富翁,但她很清楚我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她从不欺骗自己。因此,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鼓励我向文字工作的方向发展。
母亲的家庭与文字素有渊源。
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堂兄埃德温。
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因报道古巴导弹危机而声名大噪。
她常用埃德温的例子来告诉我一个有雄心的人能走多远,即使他没什么天赋。
“埃德温·詹姆士虽然打字速度比较快,但他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你看,他现在多么功成名就,”我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早就认定我有文字天赋,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目标,她的整个生命便开始围绕着帮助我开发天赋而运转。
虽然很穷,她还是为我们订了一套适合中高级水平读者阅读的读物。
每个月都会有一本书邮寄过来,价值39美分。
然而,我感兴趣的却是报纸。
我贪婪地汲取每一条消息: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怕的事故、在遥远地区发生的战争对人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以及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的消息。
警察贪污以及凶手死于电椅的报道令我着迷。
1947年,我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向《巴尔的摩太阳报》应聘警事记者一职。他们为何选择了我是个谜。
工资是一周30美元。
我抱怨薪水太低,这对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是侮辱,但母亲却不认同。
“如果你努力做好这份工作,”她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名堂来。”
不久,我被委派去采访非洲各国驻美大使馆的外交官。
工作七年后,《太阳报》派我去白宫采访。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能够从椭圆型办公室发回报道已经是达到职业的顶峰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我期待着从她的脸上看到喜悦。
但要是我能够考虑到她为我设定的不断向前迈进、向上攀升的人生路线,我就不该有这种期待了。
“好,拉斯,” 她说:“要是你努力做好这份白宫的工作,你有可能会有所成就。”
母亲并没有对我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无论我做什么,我取得的成就在她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往往会让我心烦。她从不向我道贺,从不承认我做得很棒。
即使在我成功的时候,她也是说一些否定的话。
“即使你到达了巅峰,你还得留神。”她总是尖刻地指出,“成就越大,摔下来也越重。”
在我刚刚成为记者的几年中,舅舅埃德温的成就常常萦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常想,要是《纽约时报》雇用我,该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那样我就可以向母亲一劳永逸地证明我的价值了。
后来,连孩提时代也没想过的是,《纽约时报》竟然自己来敲门了。
可惜的是,当我去《纽约时报》工作时埃德温舅舅已经离开了那里。
最后,我终于被委任了一个记者能够梦想得到的最具荣誉性的工作:《纽约时报》的一个固定专栏的评论员。
这证明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制定的、鼓励我从事笔墨生涯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1979年,我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获得了一个重大奖项──普利策奖。
不幸的是,在这前一年,我母亲的神志和健康状况都完全崩溃了,她住进了疗养院,从此与世隔绝。
她从来不知道我的普利策奖。
我大概可以猜到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错,孩子。看来,要是你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标签: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