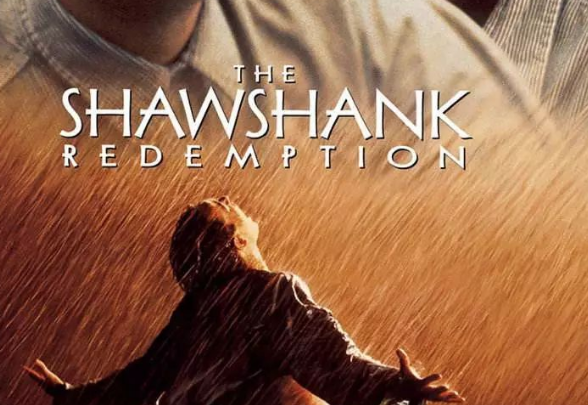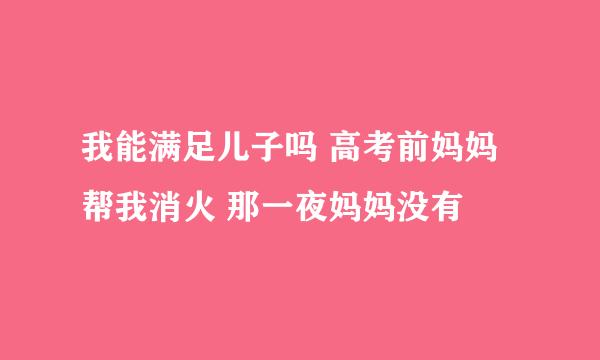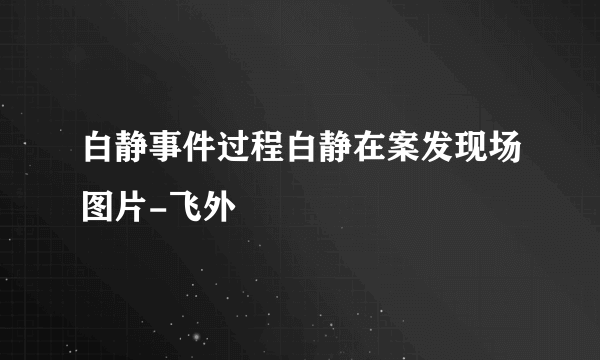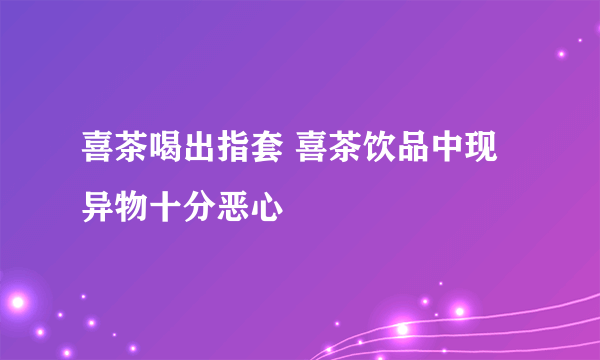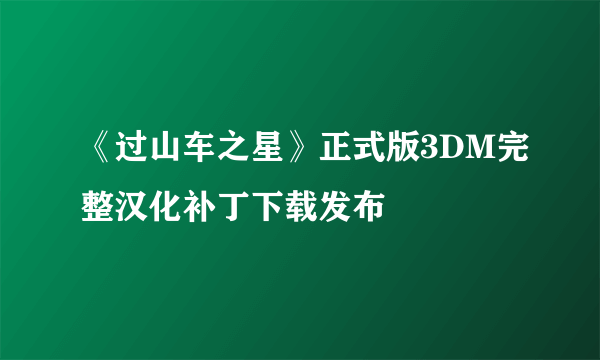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长长的巷道一眼望不到头,像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眼巴巴地等着吃人。逼仄,昏暗,潮湿,这么多年这里好像一直没有修整,还是记忆里那个可怕的样子。空气中充斥着压抑恐怖的气息,窸窸窣窣的声音无处不在,好像是风在窃窃私语,又好像,是人在窃窃私语。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发誓一生都不要再回来的地方。
兴许是偶然,又兴许太久没来这座城,想起了那个早已埋葬在内心的人了吧。
在这个不算发达的小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阴暗的角落,我在这里出生。然而没有人会因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而感到欣慰,因为我注定一生背着赎罪这两个字。
我的母亲,别人都说她是一个疯子。毕竟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把农药灌进熟睡的父亲嘴里,而我那时已三个月了吧。
她生下了我,因为那是这个巷道没有法律可言,也没有人亲眼证实,她又抚养我长大,但那时,落在我和她身上的目光,总不是很让人舒服。
那个年代,那个封闭的小城市,那个阴暗的巷道,还没有道德绑架这四个字。但我上学以后,却很早很早就理解了这个词。
“你妈妈杀人,你以后肯定也杀人,杀人偿命,她没偿命,以后就偿你的命。”
你要偿命,你要偿命!像魔咒一样,驱之不散。
语言攻击很快就落伍了。
很快,他们发现了新的排挤方式,也发现了这样更能羞辱我。
落在身上的拳头是没有温度的,他们说出的话同样没有温度,尽管裸露的皮肤能感受到风吹过的寒意。
很疼。恍惚中我想。
我不叫,也不哭,像木偶一样,等着这闹剧落下帷幕。果然他们很快发现这样没有意思,三三两两离开,最后都散光了,我才敢慢慢地在地上借着月光探自己的衣服,忍着痛穿上,呆呆地愣在原地,直到母亲找来。
她很快猜到我经历了什么,泪水充斥了她的双眸,她伸出手想要抱我,我下意识地后退。她的手僵在了半空,轻颤了两下,泪水涌流,但仍然强硬地抱住我,哽咽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任由她抱着,感受着她温暖的体温,才感觉世界原来是有温度的。
那个晚上,我们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久到那个巷道似乎都亮了几分。
我休学了。母亲决定要带我离开这里。她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工作,我开始整天整天地见不到她。然而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她就病倒了。
被人辱骂我没哭,被人欺负我没哭,这么多年无论怎样我都没哭,可当我就坐在那里握着她的手,她就静静看着我。她的手是暖的,暖暖的,我就那样哭了出来,我已不记得那是到底哭了多久,似乎连着这几年的份都一起哭掉了。
那个晚上母亲给我讲了很多很多她的故事,比如说,她是被拐到这个城市的,比如说,常年家暴她的父亲。
我没有办法给母亲治病,无论我怎么求她,她也不愿意把她存的钱拿出来。我只能一天一天地看着她消瘦,一天一天地无力地看着。我总是握着她的手,感受着她的温度,还是那么暖,世界却一天一天地冰冷了下去。
母亲走了。
我也沉寂了下去。
我拿着母亲临死前给我的钱,很快逃离了那个城市。
一晃,这么多年,仍然觉得害怕。
我一边想,一边穿过了那个巷道,今天是母亲的祭日,墓碑,墓碑,墓碑在……
我不由得顿住了。
阳光一点一点从黑暗的夹缝中探出脑袋来,母亲的墓碑在阳光下熠熠地闪着光。
很干净,像面无暇的镜子,能看见我带着泪痕的面庞,碑上圈着很多花环,洁白,美丽。
风还挺好。
标签: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