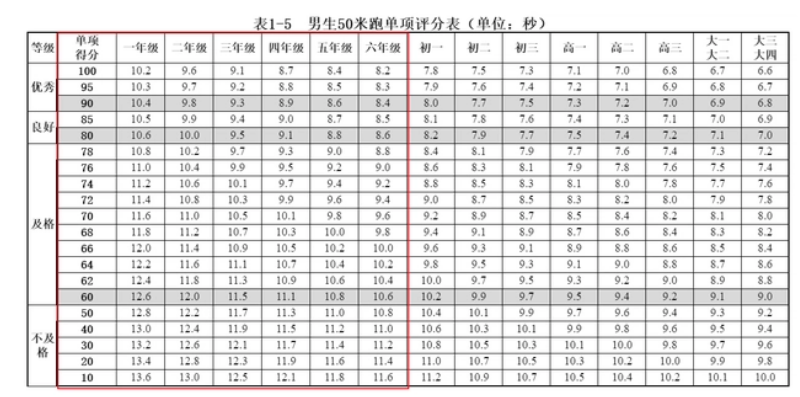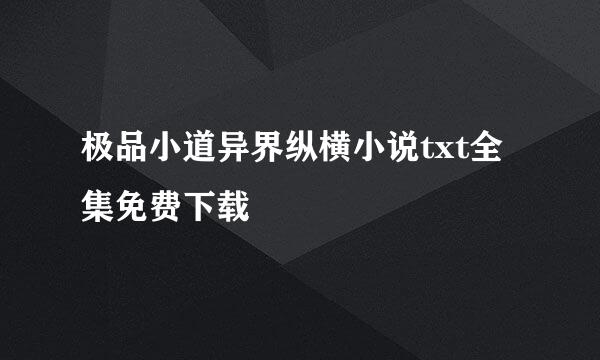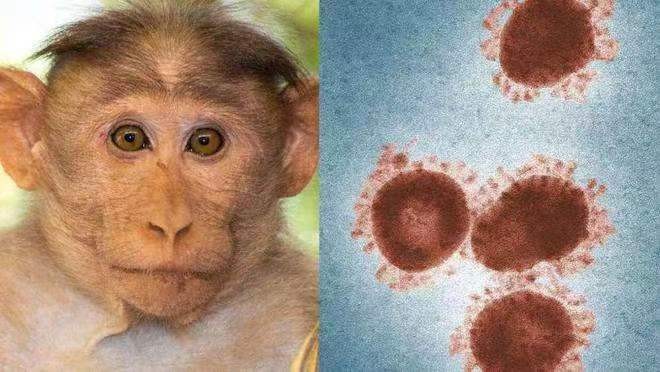《一日的春光》冰心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 今年北平的春天来的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阴,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的远引了。 天下事都是如此—— 去年冬天是特别地冷,也显得特别地长。每天夜里,灯下孤坐,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气。一冬来,一切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安慰自己说:“等着罢,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很远么?” 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宴稿漏的行列,排得意外地长,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 九十天看看过尽——我不信了春天! 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杏花去罢。”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曾得到春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转到了大工,向阳的山谷之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花蕊相间的情态了。 我想,“春去了就去了罢!”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分悼惜,七分憎嫌,总之,我不信了春天。 四月三十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看海棠,“且喜天气晴明”——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惟一的春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欣然地答应了。 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还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边的那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烘烘的在繁枝上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都消失了。喜悦地仰首,眼前是烂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恣情的一放! 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敬凯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斯,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 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了酬报,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着脸,低着头,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林清玄的: 美丽的心 在一个演讲会上,一位听众问我:“林先生,我发现来听你演讲的人,不论男女部 长得很美丽。我想请问你,是美丽的人特别喜欢读你的书呢,还是读了你的书会变得美 丽?” 由于他的问题如此突兀,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我说:“你看到这些人这么美丽,那是晌烂因为你有美丽的心来看他们,就像现在我们 看着你,觉得你也十分美丽呀!” 演讲完后,我沿着夜黯的公园走回家,发现在月色中的公园也非常的美丽,花树温 婉,池水浮金,空气中流着花香,是呀!这世界如是美丽,有的人特别容易看见,是缘 于他们有美丽的心。 令人遗憾的是,通常我们只看见公园的美丽、花与树的美丽,月亮与星星的美丽, 很少人去看见别人的美丽,去看见那在街头、在餐厅、在很多很多地方的许多美丽的心。 我的写作,不只是在告诉人关于这人间的美丽,而是在唤起一些沉睡着的美丽的心。 澈如水晶 从花莲回来,走苏花公路,到崇德隧道口附近,看到几个工人在排石板阶梯,他们 专注的神情吸引了我,我便下车了。 工人用一种近乎悠闲的样子排石板梯,他完全不用水泥或任何粘接物,他只是把造 型都不同的石板沿山坡调整,让石板密实在山坡上,并与下一个石板接合。 这看起来不甚费力的工作,事实上是孕含了极独运的匠心,以及全副的精神,工人 必须要完全了解每一块大小不同的石板和每一寸不同斜度的山坡才做得到。 不远处,就是海了,一层青、一层蓝、一层靛的,完全没有污染的海。 “这石阶可以通到海边吗?”怕惊扰了他的工作,我小声的问工人。 他正一分一分地挪着手上的石块,约三十秒后,他头也没抬地说:“往下走,转两 次弯,就到海边了。” 我兴奋地沿石阶跳跃而下,心情欢愉像一个孩子,我发现阶梯的两旁开满牵牛花, 比平常看到的还要硕大,是最美丽的浅紫色,色泽清丽,还带着今天清晨的露水。 到了海边,看到海岸的卵石美丽不输给牵牛花,粒粒皆美,独一无二。一艘渔船正 顺着波浪在海岸不远处载沉载浮。 我蹲下来捡石头。 我向来都喜欢海边的卵石,因为这些石头从来没有隐藏,也不故意显露,它只是在 海岸如实呈现它的美与风采。它不怕人笑,也不排斥别人的掌声。 这石头、这海洋、这路边的牵牛花、这专心排石阶的工人,都如是如实地在演出自 己,既没有隐藏,也没有显露。这样一想,使我震惊起来:呀!呀!原来我们身边最美 的事物,无不如实、明白、澈如水晶。 只可惜这水晶映现的沛然万象,凡俗的眼睛都把它当玻璃来看待。 如果我们要看见这世界的美,需要有一对水晶一样自然清澈的眼睛;如果我们要体 会宇宙更深邃的意义,则需要一颗水晶一样清明、没有造作的心。 百年含笑 在乡间的庭院,一个老人带我去看一棵百年的含笑花,说那是他的父亲亲手栽植的。 那百年含笑的高大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含笑花只有几尺高,百年的 含笑花竟有两三丈高。 更令人惊奇的是,那棵高大的含笑,花朵开得密密麻麻,香气之盛有如一座香水工 厂,方圆几尺的地上都被洁白的含笑花瓣铺满了。 我想到小时候家里种的几棵含笑,盛开时,我最喜欢摘一些放在铅笔盒、放在书包、 放在口袋中,走到哪里就香到那里。含笑花的香有渗透力,有时春天过去很久,含笑都 谢尽之后,铅笔上还留着春天时含笑的香味,使我写字时有着欢喜的心情。 正在出神的时候,听到老人说:“这百年的含笑开得和它第一次开时一样的香,我 如果能像它一样,百年之后也能含笑归土,就好了!” 我说:“阿伯仔,这没有什么问题,你一定可以含笑归土的。” 老人笑了,笑得就如一朵含笑花,那么洁白、纯真,散发着香气。 “不管生命的历程变成怎样,我们每天每天都要含笑开放,让香气飘扬呀!”—— 看着老人的笑,我心里这样想着。 水中的蓝天 开车从莺歌到树林,经过一个名叫“柑园”的地方,看到几个农夫正在插秧。由于 太久没看到农夫插秧了,再加上春日景明。大地辽阔,使我为那无声的画面感动,忍不 住下车。 农夫弯腰的姿势正如饱满的稻穗,一步一步将秧苗插进水田,并细致敬谨的往后退 去。 每次看到农人在田里专心工作,心里就为那劳动的美所感动。特别是插秧的姿势最 美,这世间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向前的,惟有插秧是向后的,也只有向后插秧,才能插出 笔直的稻田;那弯腰退后的样子,总使我想起从前随父亲在田间工作的情景,生起感恩 和恭敬的心。 我站在田岸边,面对着新铺着绿秧的土地,深深的呼吸,感觉到春天真的来了,空 气里有各种薰人的香气。刚下过连绵春雨的田地,不仅有着迷蒙之美,也使得土地湿软, 种作更为容易。春日真好,春雨也好! 看着农夫的身影,我想起一首禅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是一首以生活的插秧来象征在心田插秧的诗。意思是惟有在心田里插秧的人,才 能从心水中看见广阔的蓝天,只有六根清净才是修行者惟一的道路;要趣人那清净之境, 只有反观回转自己的心,就像农夫插秧一样,退步原来正是向前。 站在百尺竿头的人,若要更进一步,就不能向前飞跃,否则便会粉身碎骨。只有先 从竿头滑下,才能去爬一百零一尺的竿子。 人生里退后一步并不全是坏的,如果在前进时采取后退的姿势,以谦让恭谨的方式 向前,就更完美了。 “前进”与“后退”不是绝对的,假如在欲望的追求中,性灵没有提升,则前进正 是后退,反之,若在失败中挫折里,心性有所觉醒,则后退正是前进。 农人退后插秧,是前进,还是退后呢? 甲得从前在小乘佛教国家旅行,进佛寺礼拜,寺院的执事总会教导,离开大殿时必 须弯腰后退,以表示对佛的恭敬。 此刻看着农夫弯腰后退插秧的姿势,想到与佛寺离去时的姿势多么相像,仿佛从那 细致的后退中,看见了每一株秧苗都有佛的存在。 “青青秧苗,皆是法身”,农人几千年来就以美丽谦卑的姿势那样的实践着。那美 丽的姿势化成金黄色的稻穗,那弯腰的谦卑则化为累累垂首的稻子,在土地中生长,从 无到有、无中生有,不正是法身显化的奇迹吗? 从柑园的农田离开,车于穿行过柳树与七里香夹道的小路,我的身心爽然,有如山 间溪流一样明净,好像刚刚在佛寺里虔诚的拜过佛,正弯腰往寺门的方向退去。 空中的蓝天与水中的蓝天一起包围着我,从两颊飞过,带着音乐。 鲁迅: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 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 忽然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 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 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 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 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 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 San 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 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o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茫茫的东 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 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 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 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 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茨威格:世间最美的坟墓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列夫·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将被后代怀着敬仰之情来朝拜的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阴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坟墓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他的外孙女跟我讲,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听保姆讲过一个古老传说,提到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们俩就在自己庄园的某块地上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被忘掉了。托尔斯泰晚年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从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当即表示愿意将来埋骨于那些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 后事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坟墓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它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到被自己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大声说话。夏天,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或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打动人心的了。老残军人退休院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沉,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巨人树 (美)斯坦贝克 我在巨人树身边过了两天。这儿没有旅客,没有带着照相机吵闹的人群,只有一种大教堂式的肃穆。也许是那厚厚的软树皮吸收了声音才造成这寂静的吧!巨人树耸立着,直到天顶,看不到地平线。黎明来得很早,直到太阳升得老高,辽远天空中的羊齿植物般的绿叶才把阳光过滤成金绿色,分作一道道、一片片的光和影。太阳刚过天顶,便是下午了,紧接着黄昏也到了。黄昏带来一片寂静的阴影,跟上午一样,很漫长。 这样时间变了,平时的早晚划分也变了。我一向认为黎明和黄昏是安静的。在这儿,在这座水杉林里,整天都很安静。鸟儿在蒙胧的光影中飞动,在片片阳光里穿梭,像点点火花,却很少喧哗。脚下是一片积聚了两千多年的针叶铺成的垫子。在这厚实的绒毯上听不见脚步声。我在这儿有一种远离尘世的隐居感。在这儿人们都凝神屏气不敢说话,深怕惊扰了什么——怕惊扰了什么呢?我从孩提时代起,就觉得树林里有某种东西在活动——某种我所不理解的东西。这似乎淡忘了的感觉又立即回到我的心里。 夜黑得很深沉,头顶上只有一小块灰白和偶然的一颗星星。黑暗里有一种呼吸,因为这些控制了白天、占有了黑夜的巨灵是活的,有存在,有感觉,在它们深处的知觉里或许能够彼此交感!我和这类东西(奇怪,我总无法把它们叫作树)来往了大半辈子了。我从小就赤裸裸地接触它们。我能懂得它们——它们的强力和古老。但没有经验的人类到这儿来却感到不安。他们怕危险,怕被关闭、封锁起来。怕抵抗不了那过分强大的力。他们害怕,不但因为巨衫的巨大,而且因为它的奇特。怎呢能不害怕呢?这些树是早侏罗纪的一个品种的最后的孑遗,那是在遥远的地质年代里,那时巨衫曾蓬勃繁衍在四个大陆之上,人们发现过白垩纪初期的这种古代植物的化石。它们在第三纪始新纪和第三纪中新纪曾覆盖了整个英格兰、欧洲和美洲。可是冰河来了,巨人树无可挽回地绝灭了,只有这一片树林幸存下来。这是个令人目眩神骇的纪念品,纪念着地球洪荒时代的形象。在踏进森林里去时,巨人树是否提醒了我们:人类在这个古老的世界上还是乳臭未干、十分稚嫩的,这才使我们不安了呢。毫无疑问,我们死去后,这个活着的世界还要庄严地活下去,在这样的必然性面前,谁还能作出什么有力的抵抗呢? 真实的高贵 (美)海明威 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每个人都是领航员。但是,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以最幸福的人的生活为例——它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麻线,丧亲之痛和幸福祝愿彼此相接,使我们一会伤心,一会高兴,甚至死亡本身也会使生命更加可亲。在人生的的清醒时刻,在哀痛和伤心的阴影之下,人们真实的自我最接近。在人生或者职业的各种事务中,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不如心情,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在一个看来奢华浪费的年代。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之微小的。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树之赞(德)黑塞 树,是予我以谆谆教诲的传道士。我崇敬每一棵树,不论它们是以麇集方式还是以家族方式生活的树,也无论它们是生长在莽莽原始森林之中还是小片树林里。然而最使我崇拜的还是那孤独矗立的参天大树!它们犹如一位孤寂之人,却不是因某一弱点而遁世隐居的君子,而是如同被置于孤独之境地的伟大人物,就像贝多芬,就像尼采。它们的树梢飒飒作响着整个世界,它们的根须静卧于永恒之中。但它并不沉醉在这永恒之中,而是终其毕生精力追求一个目标:完成它们与生俱有的并居于它们之中的品质道德,树立自己的形象,表现自我。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像一株挺拔茁壮的大树那样神圣、那样完美无缺。倘若有一棵被锯倒的大树在阳光下裸露着它那致命的伤口,那你就可以在那鲜亮的树桩——也是它的墓碑上读到它的整个历史:那一圈圈年轮和一个个疤痕忠实地记录着它所经历的每一次搏斗、每一次疾病和每一次痛苦,当然还有全部的幸福。它们记录着它的整个成长过程,既有那饥贫的年头,也有那丰盈的岁月,还有那每每战胜的袭击和回回挺过来的风暴。因而,每一个农民的儿子都懂得,最坚硬的树木,从而也是最珍贵的材料,其年轮最紧密。他们知道,在那高山之巅历尽险恶生长的大树,才是那坚不可摧、雷霆万钧、为世楷模的栋梁之材。 每一棵树都是神圣之物,谁能和它们谈心,谁能倾听它们的心曲,谁就能返璞归真。它们不是向你喋喋不休地唠叨什么训诫和丹方,它们撇开个别现象,向你谆谆教诲生命的原始真谛。 这一棵树会告诉你:我身体之中蕴藏着一颗核心,一束火花,一个思想,我是永恒生命中之生命。敢于尝试、敢于成功——永恒的母亲和我共同冒着危险而取得的成功,这就是我的与众不同之处;我的形体、我皮肤上的血管、脉络同样举世无双;我的眼睫毛——叶片的微微颤动,还有皮肤上那些小小的疤痕更是绝无仅有。我的天职就是:用典型的个性去塑造永恒、表现永恒。 那一棵树又会告诉你:我的力量就是信任。我对我的前辈一无所知,我对每年由我而生的千千万万子孙也一无所知。我毕尽终生体验我种子中的全部奥妙,舍此别无他求。我相信,上帝在我之中。我相信,我的任务神圣无比,我就生活在这信赖之中。 倘若我们忧伤,倘若我们失去了生活的力量,那么,会有一棵树告诉我们:平静!平静!看看我吧,生活不容易,生活也不难!这就是童心。让上帝与你的心灵说话,你就会安静下来。你之所以有所欲望,是因为你所走的道路把你引向背离母亲、背离故乡的地方。但是,每一步,每一天会把你重新引回母亲的身旁。故乡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故乡就在你心中,别无他处可寻。 每当我在晚风中倾听树林沙沙而响,就会有一种渴望漫游的情感攫住我的心房。你要是静静地听它多说一会儿,你就可以知道,在它们的核心处,在它们的意念之中也有这种漫游的欲望。这种欲望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是为了逃避痛苦,而是向往故乡,向往母亲的记忆,向往新的生活譬喻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引导我们走向回家的路。条条道路通往故乡,每一步都是一次诞生,每一步都是一次死亡,每一座坟茔都是母亲。 如果我们害怕我们的童心,树木就会在晚风中簌簌耳语。树林有长远的思想,既冗长又平静,因为它们的生命比我们长久。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倾听它们之前,它们比我们智慧,可是当我们学会倾听它们之后,我们思想的短暂、快速以及孩童般的急促恰恰赢得了空前的幸运。只有当你学习倾听树木之后,你才不会想成为一棵树,就会满足你的现状。这就是故乡,这就是幸福。
标签: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