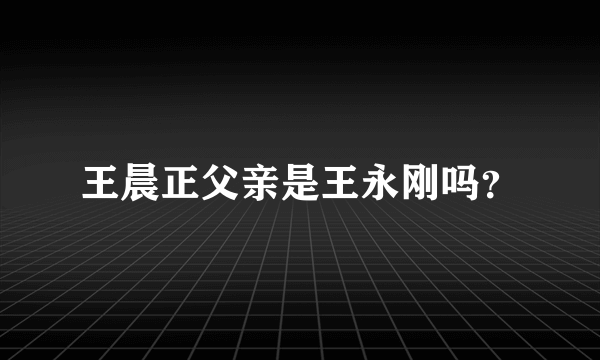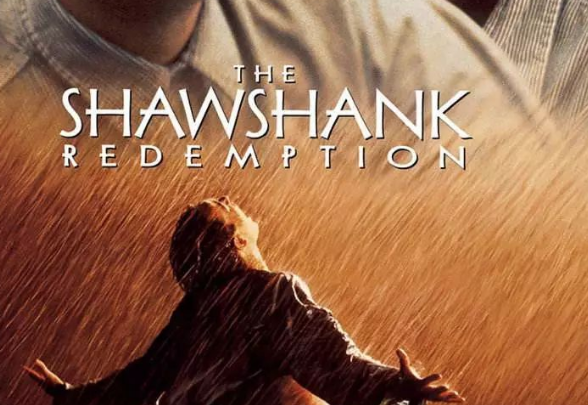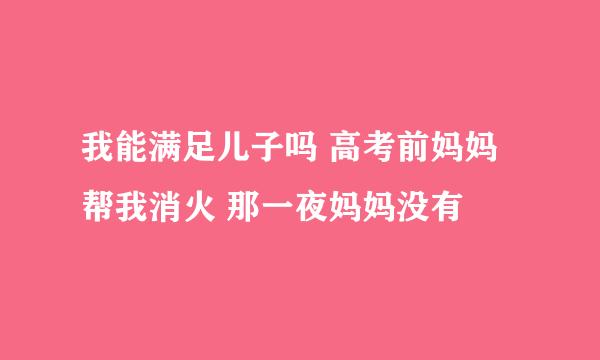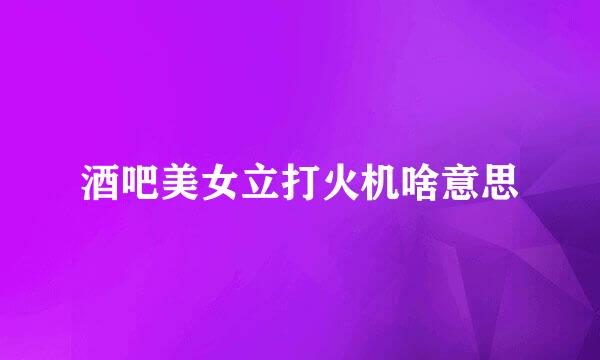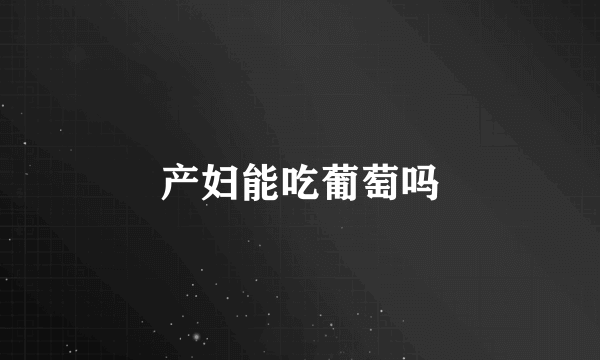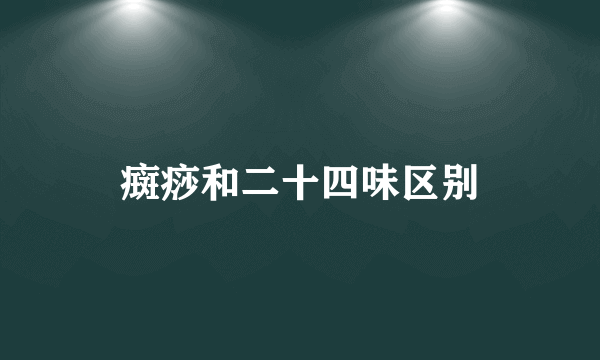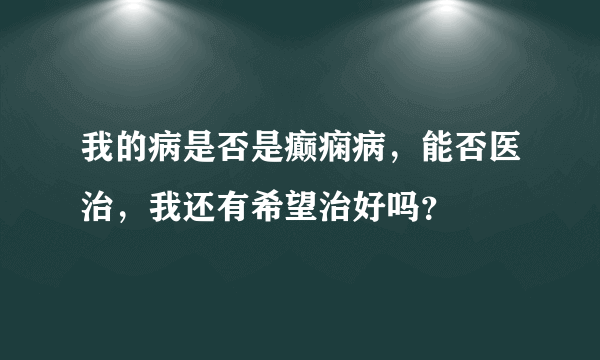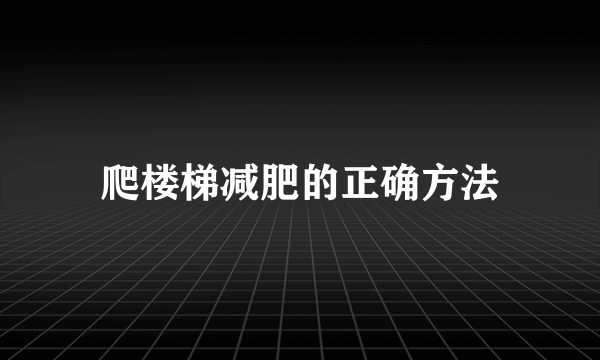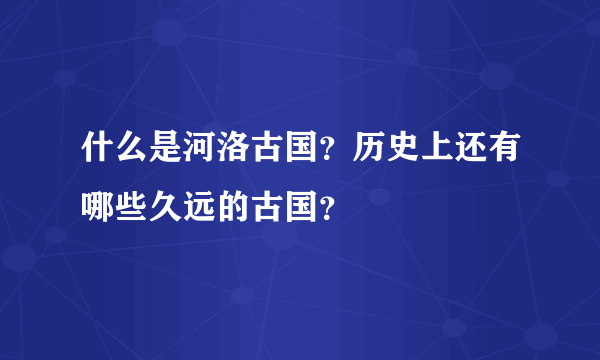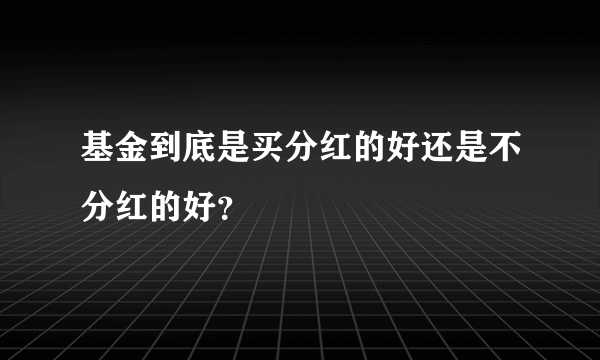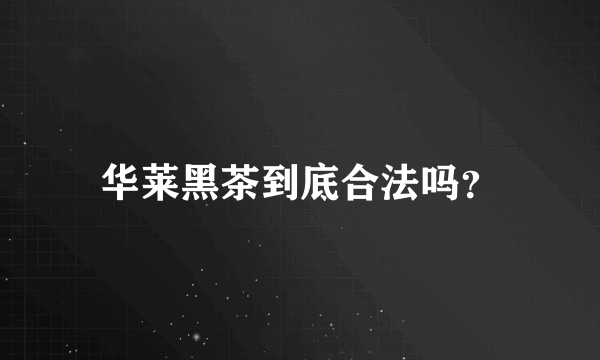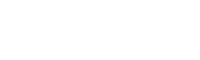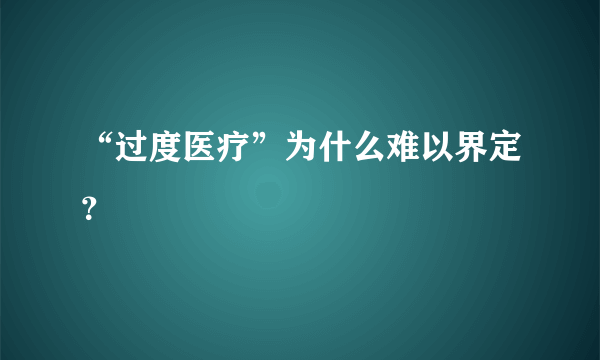
随着对“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人们已经意识到,医药费用的不断攀升其实包括了医疗服务成本的正常增长和“过度医疗”造成的额外经济负担两方面因素。
其中,前者是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物价水平正常上升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理体现,而后者作为一种不能为患者带来真正价值却增加资源损耗的负效率行为,才是加重群众负担的关键点。
“过度医疗”是不折不扣的利益分配问题
“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恰当、不规范甚至不道德地脱离病情需求而实施的医疗行为,一般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长期以来,“过度医疗”一直为医德所不容。
即将于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则将“过度医疗”上升到了法律禁止的高度。
但过度医疗在现实中并不容易界定,这主要因为医疗服务以“人”为直接服务对象,而人体构造、机理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现阶段的医学科技水平。
即使同一种疾病,每一个患者的具体病情也不完全一样,不同的医学水平、不同的病情阶段、不同的医疗机构和不同的医生所采取的诊疗方法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因而对“过度医疗”的判断长期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
从表现形式上看,“过度医疗”似乎更多是伦理道德或技术运用方面的原因。如果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则会发现其实质是不折不扣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即一方行为主体(委托人)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代理人)提供服务,授予其某些决策权,根据代理人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报酬。
在医患关系中,双方既有治愈疾病、恢复健康或挽回生命的共同目的,又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即在保证诊疗效果的前提下,患者希望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医务人员则会利用技术权力增加自己的经济收益。
在我国过去十年“基本不成功”的医改中,医药卫生领域过度市场化、从业人员收益与“创收”直接挂钩、医药费用个人负担比例过高的体制因素放大了这一矛盾,造成了医药费用超出群众承受能力的不合理增长。
“过度医疗”为什么总能被合理解释
之所以产生“过度医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医学诊疗服务为例,接受专门训练、拥有实践经验的医生掌握着患者不可能具有的专业技术信息,加之现阶段医患沟通机制不完善,使患者在医患关系中基本处于“服从”地位,几乎没有能力和渠道去行使对医疗行为的选择权和监督权。同时,生命的唯一性也会使患者特别是病情较重者产生不惜代价的想法,对待“过度医疗”只能被动地接受。在技术、费用信息双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可以采用分解收费、重复收费的对策。何况实际费用除了项目单价相对固定,其他均为医生支配下的可变量。如果不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一关键问题,再严厉的管制措施也只是增加行政资源的损耗浪费而已。
二是结果的不确定性。诊疗效果不仅仅受医生的行为和努力程度影响,也取决于其他一些不可控的随机因素。
现实中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品替代常规药品的医生,也完全能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认为疗效更可靠”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从而把道德作风问题冠冕堂皇地归咎于“技术因素”。
比如治理“大处方”常用的数据监测法,定期对用量最大、增量“不正常”的若干种药品、开药金额较大的若干名医生进行抽查。
但数量统计并不能直接得出过度用药的结论,如果某种疾病流行,相关药品的使用量自然明显增加;慕名求助某专家号的病员络绎不绝,其用药量大必然会连续上榜;由于病理、病程等原因,不同专业的药物使用也会有所不同……对此,多数医院还会组织专家作进一步的用药合理性分析。但许多分析专家自身就是开药大户,有的甚至是药事委员会成员,对药品进入医院的“细节”心照不宣,被评价对象又是同事或同行,总能以种种“合理性”解释顺利过关、皆大欢喜。
三是契约的不完备性。由于医疗过程的复杂变化,医患双方不可能将所有情况下的权力、责任事先界定清楚,没有详细规定的那部分权责配置必然会影响代理人的行为选择。
例如曾被寄予厚望的“单病种限价”,虽然有了形式上的价格“封顶”,但相同名称的“单病种”在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医院所采用的诊疗技术、流程甚至疗效判断标准都有所差异,不同医院间的“限价”缺乏可比性,也难以消除患者对服务质量“缩水”的顾虑。
有的医疗机构为了“低价”招揽病员,不切实际地压缩医疗成本,随意减少术后住院观察时间、降低出院标准等,甚至“该用纱布的用棉球,该用棉球的用棉签”,将院内感染等情况也解释为并发症,趁机跳出“封顶价”限制,反而会加重病人负担。
有没有办法解决 “过度医疗”问题
引入临床路径,可以较好地克服以上三个制约因素。
有了统一的临床路径,能够约束医务人员克服随意性行为,减少偏差失误,同时明确相关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结果不确定的问题;
患者可以熟悉治疗计划,了解哪些药物、治疗、检查项目是必须的,根据住院时间和诊疗项目对费用进行预测,打破信息分布的不对称,医保机构也可借此加强费用监管的有效性;科学的临床路径本身则是对契约不完备性的破解,既便于引导患者配合治疗,也有利于医院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临床路径最初只是美国医疗机构为应对医疗保险由后付制向按疾病诊断相关组支付变革的被动之举,后来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有效的医院质量管理工具和疾病诊疗、评估标准。
我国对临床路径的引入始于20世纪末,近年来进展迅速,特别是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单位的探索和创新,大大推动了“本土化”进程。
到2009年,临床路径试点列入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五项重点改革2009年工作安排》,卫生部在全国50家医院对112种常见疾病启动了试点。
面对当前我国医药费用增长过快、医患之间缺乏互信的现实,我们期待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路径能够在遏制过度医疗、促进有序竞争、和谐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许赫赫)
标签: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