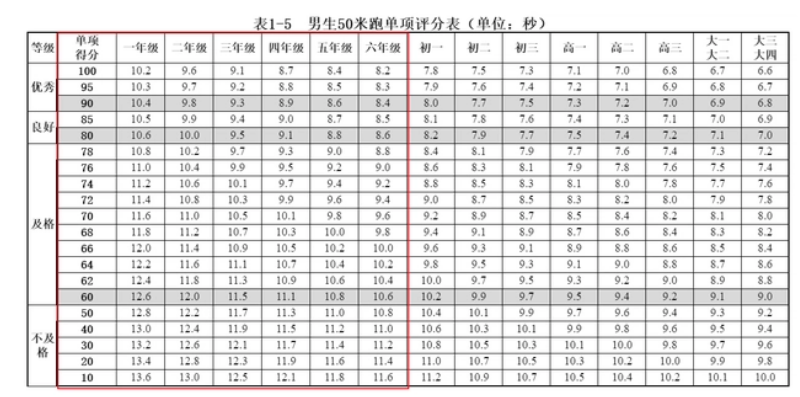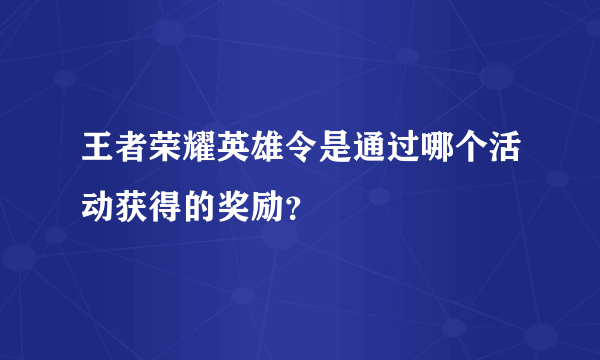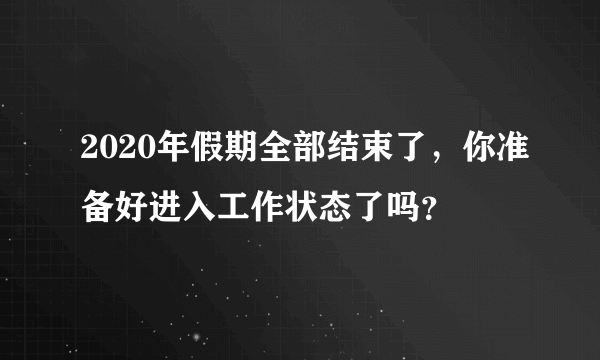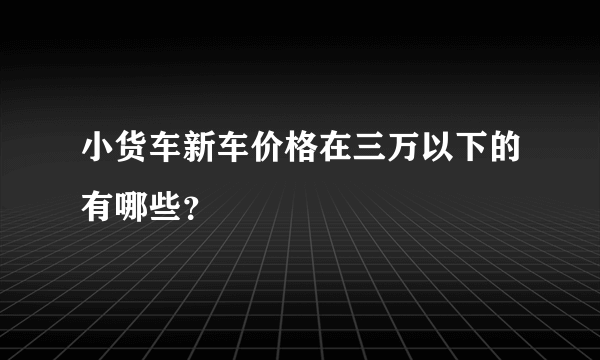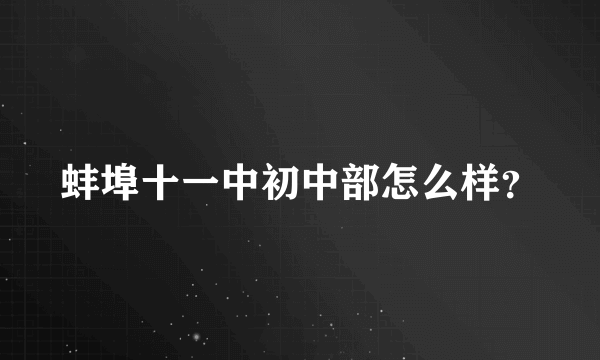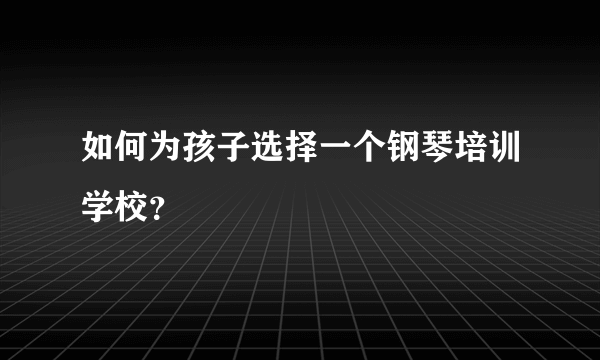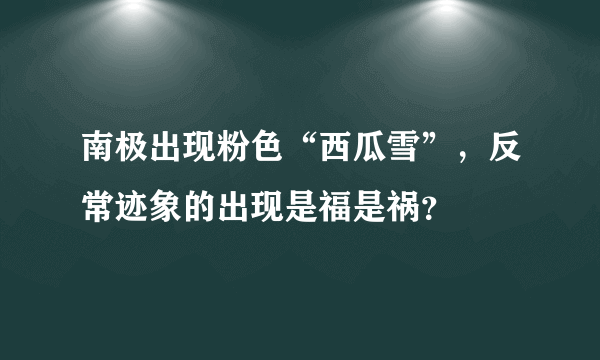“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曾经只是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一句台词, 而如今却成了我们在看到负面新闻时的悼词。
社会的发展让被遮掩的恶行越来越多地被曝光出来,同时人性的丑恶也在不断刷新我们对罪恶的认知。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少骇人听闻的事件:三月,一男子求复合不成,当街逼停前女友的红色路虎车,并强行胁迫女生上车点燃淋在身上的汽油自焚,导致两人被烧身亡;五月,一位空姐在从宾馆回市内途中被滴滴司机强奸且被砍数刀,抛尸荒野;六月,甘肃女孩糟老师猥亵患重度抑郁,生死存亡之际楼下围观者却欢呼鼓掌,直到最终悲剧发生;八月,疫苗事件爆发,等等。
所有这些事件,无论哪一件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些时事看似出发点大不相同,但实际上所有的恶行都有着一个扎根在 人性中最大的恶——缺乏共情。
共情的能力把握着人与人关系的命脉,同时也扼制着人们心中的阴暗。 当一个人失去共情而对周围的人与事麻木不仁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最大的“恶人”。
作为人,定义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结构,更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思想,其中最特别的是我们复杂的人际关系。人毫无疑问是社会动物。 当我们思考“恶”的时候,也是从社会出发,将那些破坏人际关系、伤害他人的行为定义为“恶”。
而其中,促使人们去产生且保持羁绊的原点则是共情—— 一种能够理解且分享他人情感的能力 。同时共情 也拥有多维度的含义 :
1)分享其他人的情感体验;
2)区分属于自我的情感和属于他人的情感;
3)从另一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4)情绪调节;
5)利他动机。
情感是重要的,它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共同点,是我们维系关系的纽带。通过共情,我们学会去爱,去理解,去原谅,不仅考虑自己,也会关心他人。
幸运的是,这样举重若轻的能力是我们人类天生就拥有的 。
在心理学家Martin Hoffman的理论中,两岁之前的婴儿已经能够感知别人的痛苦并作出反应(1975,2000)。一个实验测试八到十六个月的孩子是否有共情的能力。他们发现,八个月和十个月的孩子都会在母亲因为身体受伤而痛苦的时候流露出关怀之意,有时甚至是不安与轻度痛苦(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而十二到十六个月的孩子则会直接用抚摸拥抱或亲吻的方式试图安慰他们的母亲(Roth-Hanania et al, 2011)。
在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当一至九个月的孩子看见一个孩子因为不安和痛苦而哭泣的视频时,他们也会因为共情,露出相似程度的不安和痛苦(Geangu et al, 2010)。
如果人天生就拥有共情,能够体会别人的痛苦,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伤害别人呢?
其实,由于个体差异,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程度的共情。 有的人甚至天生就没有共情,比如精神变态患者 (psychopath)。实验显示,精神变态患者之所以如此残酷无情,恰好是因为他没有共情,或者说他缺少正常产生情绪和体会情绪的能力。从精神患者的脑部扫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杏仁核和脑岛这些直接与共情有联系的部位都不能正常运作(Kiehl & Buckholtz, 2010)。
精神变态患者无疑是“恶”的代表,无法修复,也难以共存。但精神变态患者是属于极少数的群体。对于普通人来说,人们 又是如何失去共情的能力的?
a).残酷的社会环境: 在西方对恐怖分子的研究中,一个贬低情感,将展露情感视为耻辱的社会会扼制共情能力的发展,从而使人对其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或成为付诸痛苦的加害者(Kobrin, 2016)。
b).不良的家庭环境: 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态度是不健康的,不管是冷漠,还是溺爱,都会扼制孩子的共情能力。还有研究显示,如果父母对孩子有虐待行为,哪怕是轻微程度,也会导致孩子对他人的痛苦产生恐惧或愤怒的情绪,甚至是攻击对方(Stern & Cassidy, 2018)。
c).黑暗人格三合一: 人格中最大的三种“恶”被统称为黑暗三合一,分别是:权术主义(Machivellianism),自恋(Narcissism),精神变态(Psychopathy)。这三种“恶”也和共情息息相关。拥有这些性格特征的人,普遍看重自我利益,乐于通过操纵、欺骗、伤害他人等方式获利,并忽略他人的感受。他们并非没有共情能力,但是他们会为了达到目的,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共情能力剥离或弱化(Doenyas, 2017)。
d).主动剥离共情——蠢蠢欲动的欲望: 被欲望催生出来的社会动机和共情能力一样因人而异。当从自身出发的社会动机和为别人考虑的社会动机产生矛盾的时候,决定了人是否会使用他们的共情能力来做出利于他人的事情,或是在认知上剥离或压制共情能力,以避免操纵他人时产生的负面情绪。
例如,魏则西事件中的医生。当个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被放在天平上衡量时,人可能会被即时的利益所蒙蔽,短暂地失去感知对方痛苦与困扰的能力。再比如校园暴力。青少年对于社会地位的渴求越高涨,他们的共情能力越低,越容易伤害别人(Doenyas, 2017)。
e).被动剥离共情——环境的影响: 比如,网络暴力。在线下生活中不会对人诉诸暴力的人,可能会在网络上露出最丑恶的嘴脸,说出最恶毒的话。这是因为在网络暴力中,加害者和受害者并非处于同一空间,物理距离拉远了心理距离,加上隔着屏幕加害者无法通过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直面受害者的痛苦,这使得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难以共情。
这也能够解释最近甘肃女孩跳楼事件中,为什么围观者们看上去那么冷酷无情。除去难以共情这一点,网络暴力和围观者们同时陷入了群体造成的“去个体化”现象。群体和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增加了“匿名性”,减少了对他人评价的顾忌,同时更容易推卸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无法克制内心的小阴暗,更容易展露内在的恶意(Pfetsch, 2017)。
如此一来,人性中最大的恶也许并非是特定的人群,或是某种人格, 而是我们有意识的“麻木不仁”。
偏见(prejudice)、侵略性(aggression)、和冷漠(apathy)是共情主动或被动剥离后联系最紧密、效果最显著的三个后果。
而这三个后果都能煽动人最负面的情绪,进而摧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化心理学曾提出社会关系帮助人类在艰苦的大自然环境中提高生存率。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更是影响了我们生活的优质感和幸福度。
而当我们的社会关系被负面情绪摧毁时,人便会失去社会关系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名誉,信任,他人的亲近感,等等。这与人既得的利益相比,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共情一如前文所述,能够帮助我们构建良好强大的社会关系,不仅有互利互惠的成功,也会得到精神的富足感。
随着所谓的“成长”,有许多人损失或丧失了这种“共情的能力”,从而催生诸多恶行。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拥有“人性中最本源的善意”,而这种生命初始的本能,其实最终保护的是我们自己。
以上。
References:
Doenyas, C. (2017). Self versus other oriented social motivation, not lack of empathic or moral ability, explains behavioral outcomes in children with high theory of mind abilities. Motiv Emot, 41:683–697.
Geangu, E., Benga, O., Stahl, D., & Striano, T. (2010). Contagious crying beyond the first days of life.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33, 279–288.
Hazebroek, Babette C. M. van, Olthof, Tjeert, & Goossens, Frits A. (2017). Predicting Aggression in Adolescence: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a Lack of) Social Goals. Aggressive Behaviour, 43: 204–214
Hoffman, M. L. (1975). Developmental synthesis of affect and cognition and its interplay for altruistic motiv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1, 607–622.
Hoffman, M. L. (2000).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fetsch, J. (2017). Empathic Skills and Cyberbullying: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Measures of Empathy to Cyberbullying in Comparison to Offline Bullying Among Young Adult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8, 58-72.
Kiehl, Kent A., & Buckholtz, Joshua W. (2010). Inside the Mind of A Psychopath. Scientific American Mind, 22-25.
Kobrin, Nancy H. (2016). Nobody Born a Terrorist, But Early Childhood Matters: Explaining the Jihadis' Lack of Empathy.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10: 108-111.
Roth-Hanania, R., Davidov, M., & Zahn-Waxler, C. (2011). Empathy development from 8 to 16 months: Early signs of concern for others.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34: 447–458
Stern, J. A., & Cassidy, J. (2018). Empathy from infancy to adolescence: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evelopmental Review 47, 1–22.
Tousignant , Béatrice, Eugène, Fanny, & Jackson, Philip L. (2015).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the neural bases of human empathy.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48, 5–12.
点击查看过往高赞回答:
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
有哪些常人不知道的「常识」?
人在迷茫时该干什么?
戳此免费领取: 心理学习资料包
标签: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