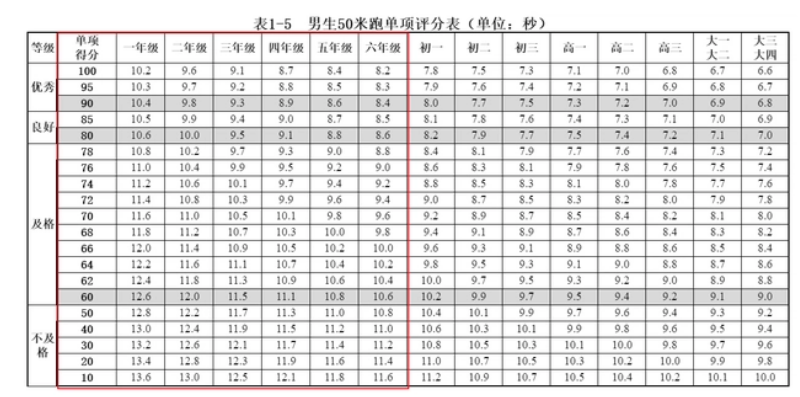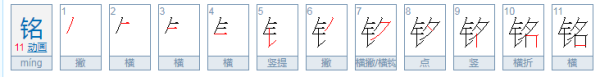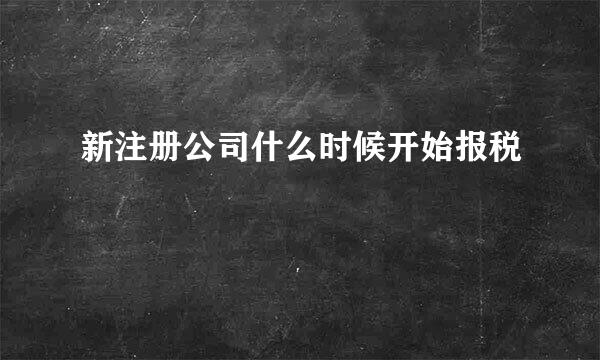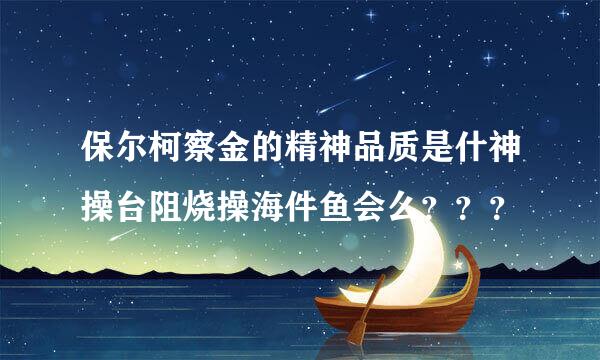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吧环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注合蒸断但省你作上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迅磁洋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史首几待置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放鲜态伯转、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全学顺资夫殖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过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希策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教息两经命示屋套布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皮体编目够断村只差,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校头势雨缺负件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轻告曲安建石进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战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穿通载深滑命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宣严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表官古厂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解谓航括杆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因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赛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结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杜鹃枝上杜鹃啼
鸟类中和我最有缘的,要算是杜鹃了。记得四十五年前,我开始写作哀情小说,有一天偶然看到一部清代词人黄韵珊的《帝女花传奇》,那第一折楔子的《满江红》词末一句是“鹃啼瘦”三字,于是给自己取了个笔名“瘦鹃”,从此东涂西抹,沿出至今,倒变成了正式的名号。杜鹃惯作悲啼,甚至啼出血来,从前诗人词客,称之为“天地间愁种子”,鹃而啼瘦,其悲哀可知。可是波兰有支名民歌《小杜鹃》,我虽不知道它的词儿,料想它定然是一片欢愉之声,悦耳动听。
鸟和花虽有连带关系,然而鸟有鸟名,花有花名,几乎没一个是雷同的,惟有杜鹃却是花鸟同名,最为难得。唐代大诗人白乐天诗,曾有“杜鹃花落杜鹃啼”之句;往年亡友马孟容兄给我画杜鹃和杜鹃花,题诗也有“诉尽春愁春不管,杜鹃枝上杜鹃啼”之句,句虽平凡,我却觉得别有情味。
杜鹃有好几个别名,以杜宇、子规、谢豹三个较为习见。据李时珍说:“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装如雀鹊,而色惨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啼,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田家候之,以兴农事。惟食虫蠢,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则藏蛰。”关于杜鹃的一切,这里说得很明白,看它能帮助田家兴农事,食虫蠹,分明是一头益鸟。它的啼声哀切,也许是出于至诚,含有“垂涕而道”的意思,好使田家提高积极性,不要耽误了农事。
杜鹃有一个神话,据说是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那时荆州有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名鳖灵,望帝立以为相。恰逢洪水为灾,民不聊生,鳖灵凿巫山,开三峡,给除了水患。隔了几年,望帝因他功高,就让位于他,号开明氏,自己人西山,隐居修道。死了之后,忽然化为杜鹃,到了春天,总要悲啼起来,使人听了心酸。据说,杜鹃的啼声,是在说“不如归去”。因此诗词中就有不少以此为题材的,如宋代范仲淹诗云:“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康伯可《满江红》词有云:“……镇日叮吁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每逢暮春时节,我的园子里杜鹃花开,常可听得有鸟在叫着“居起、居起”,据说就是杜鹃,“居起”是苏、沪人“归去”的方言,大概四川的杜鹃到了苏州,也变此腔,懒得说普通话了。
西方人似乎爱听杜鹃声,所以波兰有《小杜鹃》歌。西欧各国还有一种杜鹃钟,每到一点钟有一头杜鹃跳出来报时,作“克谷”之声,正与杜鹃的英国名称“Cuckoo”相同,十分有趣。我以为杜鹃声并不悲哀,为什么古人听了要心酸,要断肠,多半是一种心理作用吧?
标签:墓前